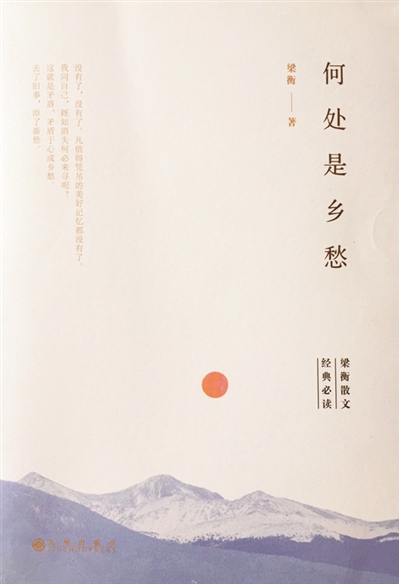书的封面上有8个字:“梁衡散文 经典必读”。想想也是,书那么多,就得挑着来读。现在购书只能凭封面封底简短的文字介绍,就将封底冯牧的一段话放在此地:“梁衡作品体现了对自然山川美、历史文化美、生活真谛美、语言文采美的追求。《晋祠》等作为范文收入中学课本,其思想内容、审美观点、遣词造句都无可挑剔,无愧于‘教科书水平’。”我也提上一笔,梁衡为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,这就让我觉得当下正值抗疫,线上教课,若能在家里读读他的文字,或对学习是有益处的。
《何处是乡愁》是本书首篇文章,作者将此文题当作书名,可略窥他的心结与情感。梁衡写道:“乡愁,这个词有几分凄美。原先我不懂,故乡或儿时的事很多,可喜可乐的也不少,为什么不说乡喜乡乐,而说乡愁呢?最近回了一趟阔别六十年的故乡,才解开这个人生之谜。”先看他小时候生长的环境,真是中国山水画里的景象。“故乡在霍山脚下,一个古老美丽的小山村,水多,树多。村中两庙,一阁一塔,有很深的文化积淀。我家院子里长着两棵大树,一棵是核桃,一棵是香椿,直翻到窑顶上遮住了半个院子。”后来,离开了家。一年一年地过去,童年的家,成了心里恒久不变的桃源。
作者给随行的人讲,老香椿树的根,不知何时从地下钻到了他家的窑洞里,又从炕边的砖缝里伸出几枝嫩芽,就这样无心去栽花,终日伴香眠。儿时每当小病,他母亲安慰的办法是,到外面鸡窝里收一颗发热的鸡蛋,回来在炕沿边掐几根香椿芽,咫尺之近,就在锅台上做一个香椿炒鸡蛋。那种童话式、魔术般的乐趣永生难忘。他对于炕头的记忆很多,如在旧灯下,枕着母亲的膝盖,看纺车的转动,听远处深巷里的狗吠和小河流水的叮咚。
童年的生活太要紧了,我总觉得,这段时间其实在做着一个美丽的梦,养着性情,伴到老。梁衡笔下,儿时的日子,纯真欢快,和睦温暖。他又感到,记忆中许多东西没有了,但还是要来寻,这就成了矛盾,矛盾与心成了乡愁。历史在前进,村貌在变化,只是失去的东西与情难以割舍,“同时作用在一个人身上,搅动着你心底深处的自以为已经忘掉了的秘密。”那次从故乡回到县里,主人问此行的感想,他随手写了四句小诗:“何处是乡愁,云在霍山头。儿时常入梦,杏黄麦子熟。”我想,这亦是人之常情,到了老年,好像又和童年记忆相遇。故乡永在儿时的记忆里。
说几句闲话,记得有人问黄裳先生对书话的看法。他讲,书话其实是一种随笔,一种很有文学性、很有趣味的文字,更接近于题跋。它往往不多谈书的内容,却喜欢在题跋里记琐事,谈买书经过,书肆、书商、书价、藏家,包括日常生活,都随手记下。即使抄书,为什么抄这段不抄那段,其实也是反映了作者的眼光、识见和学养的。
看来,与书相关皆成趣。再说梁衡,他有六十多篇文章入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课本。本书中的《青山不老》即是其中之一,此文写得很有气势,他道,在中国的晋西北,是西伯利亚大风常来肆虐的地方,过去,这里的风沙吹起能一直埋到城头。那里曾经“风大作时,能逆吹牛马倒行,或擎之高二三丈而坠”,“可是就在如此险恶的地方,我对面的这个手端一杆旱烟的瘦小老头。他竟创造了这块绿洲。”梁衡之文总能将满怀国家民族的忧心,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。诸如《万里长城一红柳》《中华版图柏》《燕山有棵沧桑树》,与历史人物敞开心扉对话,变得火花四溅,文字也肆意张扬起来。
让我们欣赏着并留意着。
蔡体霓-刊于2020年4月20日《今日镇海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