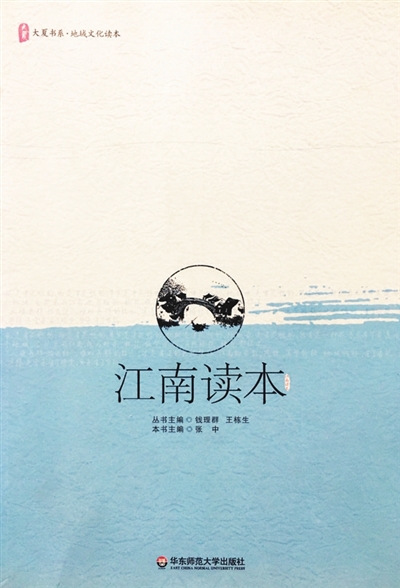地方也像人一样,有它的性格。试引一句诗来概述:“杏花消息雨声中。”杏花,春雨,正是江南地区天然的形象代表。
这里引一段鲁迅先生的文作个开头。此文选自《野草》,题为《好的故事》。文中道:“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,两岸的乌桕,新禾,野花,鸡,狗,丛树和枯树,茅屋,伽蓝,农夫和村妇,村女,晒着的衣裳,和尚,蓑笠,天,云,竹……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,随着每一打桨,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,并水里的萍藻游鱼,一同荡漾。”记文甚生动,江南景色呈现分明。
鲁迅先生的这篇文收入了《江南读本》。此书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。前面说到,江南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地理名称,唐时是“道”,宋时是“路”,清时是“省”,东汉末年还曾是“县”。《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》一书,认为大致上依明代和清代的行政区划以及当时人们的习惯,江南涉及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上海四省一市。还有《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》一书,以为经济史研究中的明清江南,应指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宁、杭、嘉、湖八府及太仓所构成的经济区。不包括今属安徽省的宣、歙两府和浙江省的绍甬两府。这些都不错。
不过,本书阐明《江南读本》不是经济史、地理史著作,而是一部文化读本。觉得观察文化,宜宽容,而不宜狭隘;宜变通,而不宜僵滞,宜顾长远,而不宜仅顾一时。于是,本书中的“江南”,就有江苏南部,安徽南部和浙江全部。还有一些对江南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少数江北城市。至于上海,更不能摒于江南视野之外。
不少名篇精编于此。潘光旦先生的《武林浏览与人文地理学》从武林(杭州)游览谈到“人文地理学”,堪称大手笔。他将江浙两地人文作详尽比较,是很有趣的视点。并谓“飞来峰”相传为飞来者,真神奇,“我辈何妨认飞来峰为一种象征之物,以为研究或鉴赏浙省人文之一助乎?”再看林斤澜先生写的《温州人》,这篇散文里有声有色地将温州人的性格刻画出来,觉得温州人近时在经济舞台上演出了一出惊人话剧。作者是写自己的故乡,更有见地。从中亦感江南文化包含之广了。
说江南,怎能不提苏州?看王蒙先生的《苏州赋》,体味他文中对于苏州是如此的情深:“不,我不能再在苏州停留。她的小巷使我神往,这样的小巷不应该出现在我的脚下面只能出现在陆文夫的小说里,梦里,弹词开篇的歌声里。弹词、苏昆、苏剧、吴语吴歌的珠圆玉润使我迷失。”还有如诗的文字:“苏州的刺绣,沉静的创造。苏州的菜肴,明亮的喜悦。苏州的歌曲,不设防的温柔。苏州的园林,恬美的诗情。苏州的街道,宁静的梦幻。”我想,去过苏州的朋友,读到此,都有同感的。
看“江南饮食”,是了解江南文化的一个佳妙的切入点。柯灵先生的这篇《酒》,就谈到绍兴人的风情,觉得酒是友情的标识,亲戚朋友在街上邂逅相逢,寒暄过后也总是这一句:“我们去吃一碗,我的。”或者说:“我们去‘雅雅’来。”——“雅雅”来,话说得这么雅致,喝酒是一种雅事便可想象了。柯灵先生亦是绍兴人。
“同朋友喝酒,嚼着薄片的雪藕,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。”叶圣陶先生的这篇《藕与莼菜》,一开头,就有思乡之情了。他想到家乡的藕,“觉得家乡可爱极了,因为在故乡有所恋,而所恋又只在家乡有,便萦着系着不能离舍了。”读本中的“江南娱乐”首篇为文载道的《故乡的戏文》,说他家乡浙东岛上的乡间庙戏,戏班来源皆须仰诸甬邑,称“宁波班”,实即昆腔,仅赖笛子而无弦索,多演文戏。文载道即是金性尧先生,他曾说过,读书动笔,动笔读书,受益匪浅。
蔡体霓-刊于2022年1月18日《今日镇海》